 電影的熟悉與陌生:側寫錦興國小《溫心港灣》座談
電影的熟悉與陌生:側寫錦興國小《溫心港灣》座談
撰文:王冠人(影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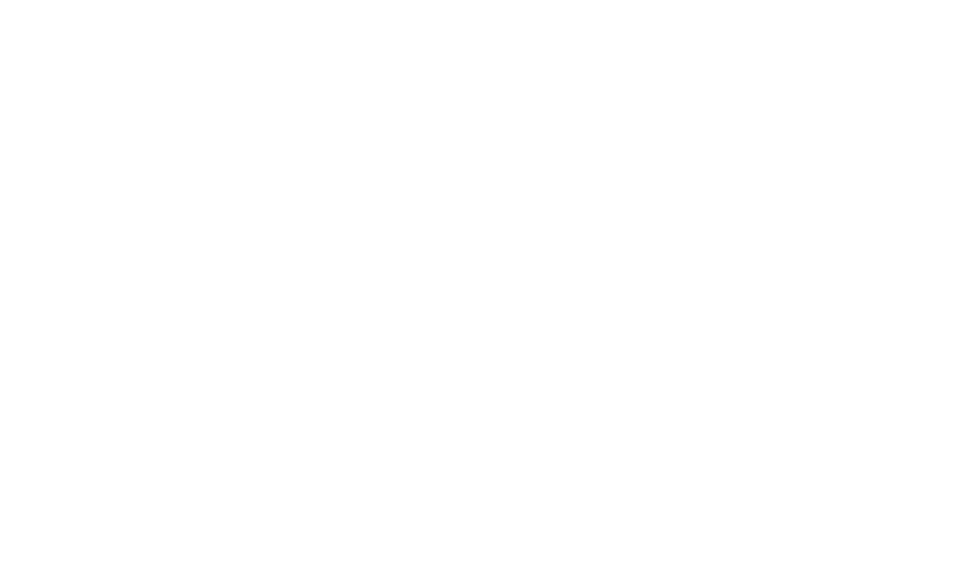
校園裡的熟悉印象
座談當天(6/7),桃園的下午正迎來充足的日照。學校附近的早餐店已入尾聲,正做著收拾工作。活動召集的教師、同行的國影中心夥伴和我,三人一起走入校園。依稀記得門口掛著少棒隊的錦旗和招生消息。
走過穿堂、低矮的迴廊和課桌教室,頗令人聯想到《囧男孩》描繪的場景:騙子一號、二號的遊戲、穿梭和窺探,和師生之間的應對。平時台前講課的老師,現在卻坐在座位上,此情景也引來學生的好奇圍觀。然而,粉筆和墨綠黑板,如今換成電子黑板。不變的是,座談中間,偶有上下課鐘聲和廣播,進行著或集體、或個別的提醒和叮囑。
這次的電影講談,約有七、八位成員參加,看的是《溫心港灣》,一部「芬蘭導演拍的法語片」。映前的準備很簡單,其中一題,是請大家做些自由聯想,關於法國和芬蘭印象:
芬蘭:千湖之國、極光、永晝、赫爾辛基、緩慢、深度、高物價、社會福利、沒有資優生的教育、NOKIA、聖誕老人
法國:恐怖攻擊、法國大革命、巴黎、文藝復興、奧塞美術館、羅浮宮、LV、髒亂、細緻、好聽的法文、浪漫、風格、質感、驕傲、馬可龍、酒、終極殺陣、悲慘世界、刺蝟的優雅、繼承人生
上列關鍵字,來自基層教師的回應,同時也勾勒出我們在台灣,透過大眾傳播和體制教育的薰陶,對於異地/異文化不同面向的理解和想像:地景風情、藝文創作、生活感受和社會氣氛。因而,或許可預期的是,《溫心》這部相對而言較小眾的電影,在這類以彼此熟悉的成員為基礎的校園社團、小團體聚會的觀影模式下,可以是一次陌生的經驗。
銀幕內的陌生景觀
成員們感到陌生的原因,並非來自片中的「議題」,譬如移民、金錢和資本,而較多是源自影片「風格」。映前作業的第二題,便嘗試請大家回憶與前述主題相關的影視和藝文作品:
移民:《歡迎來到德國》、《甜蜜蜜》以人物和情感刻畫移民辛酸
金錢:《華爾街之狼》、《大賣空》
種族:《姐妹》、《關鍵少數》、《別叫我外籍新娘》、《光陰的故事》、《大江大海1949》
敘利亞難民潮的報導
九零年代起,導演阿基郭利斯馬基那「來自極地的冷面笑匠」的獨特印記,透過影展放映,逐漸座落影迷心中(註一)。譬如場景的調度、人物的表演,都以一種「簡約」、「節制」的面貌呈現。因而在評論中,時常與法國導演布列松或梅爾維爾的「極簡」風格,拒絕情緒渲染的手法,相互對照。而其對家庭通俗劇類型的解讀解構(雖然他映畫中的「家庭」組成常常是非典型、而毋寧說是同居的夥伴或鄰居),也常令人想起德國導演法斯賓達。這些可容後解釋。
談及本片的第一印象,有教師覺得此片非常「復古」。無論是主角的職業(擦鞋匠),畫面的光影和彩度(灰藍綠黃),配樂的選用(六零年代搖滾樂,九零年代管弦樂交響曲,法國老歌,老酒館風格手風琴旋律,芬蘭氣味的非洲藍調),彷彿都與當下的時空拉出一段距離。彷彿隱身於主流視野下的法國,有一個(以至多個)金錢匱乏、但彼此協力的「小人物」社群;他們存在的姿態,無需明言的默契與行動,如同一支十分自然地交響應和的舞曲。
有意思的是,席間卻有成員對於「勒哈弗」(Le Havre,即原文片名)的地理位置和資訊,做了一番解說。原來,熟悉感是來自旅行的親身經歷。翻開電影史的篇章,法國導演馬歇・卡內的黑白影片《霧碼頭》(Port of Shadows),正是同一地點的銀幕哀歌,或許也是《溫心》男主角命名的靈感來源。
然而,一如當代的旅行經驗,即使轉換在不同都市之間,恐怕遊歷個人內在的成分,多於外在風貌的差異與體驗。一如本片的觀影軌跡和敘述,男主角馬歇從重鎮巴黎到北方港灣,從內陸到加萊海岸,包含男孩伊弟薩在內的移民們從北非被運載到勒哈弗,(幸運的話)計畫再跨海通往倫敦。這群鄰人的互助、來自不同階層、不同家鄉背景的人們,能否真正同行,成為理解彼此的「旅伴」,似乎才是故事的重點。諷刺的是,銀幕外的現實情景是,本片取景的街景和酒吧,導演眼中少數能代表法國精神的舊區,在影片完成後,也面臨拆除。
在法國/法語的文化情境下,小說《波希米亞人》或許是個容易的連結,可從此切入去理解《溫心港灣》,甚至是巴黎這座城市可供識別的一種文化身份與精神象徵(註二)。但在台灣,除了這個詞彙延伸的含義:相濡以沫的貧困藝術家或青年,尚為大眾理解和使用,至於文本之間的呼應與對照,卻不那麼理所當然。郭利斯馬基自己據此改編的電影《波希米亞人》(1992),正是他第一部法語片。不僅班底演員也與《溫心》部份重疊,精神意涵也多有相通。
現實的位移、想像的碰撞
在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中,我嘗試以片段的放映+解說,帶著大家二次觀影,從直覺的觀感出發,重新「細讀」並賦予意義。譬如人物的出場,如何透過聲/畫處理的異/同,表達個人與環境、內外在世界的關係?非洲男孩伊弟薩第一次出場,也就是貨櫃被打開的那一場戲,一組一組陌生人物的鏡頭剪輯,莊重的服裝、神聖的面貌和「非自然」的聚光,有如一幅幅家族肖像畫,把我們想像中可能破落的棲身空間,打造、定錨為尊嚴而近乎肅穆靜謐的時刻。隨即也沒有追捕的情節,製造戲劇效果,更無紛亂與嘈雜的暴力場面。
但法律秩序或權力的複雜議題,在片中並非隱沒不談,而帶有其他面貌。譬如,身穿黑色長袍的莫內警探,始終無表情、正邪角色曖昧,一度被警政長官叫去交辦任務,緝拿非法移民到案。上級以畫外音的形式,宣告了權力的無名、無面貌,卻深切地影響人物的行動(鄰居密報、警力出動),以及我們對角色的期待和評判。才使得片末莫內突然的轉向,表面上同樣是端出權力的位階,阻擋其他警察同僚的搜查,卻與其他權力的代言者,在行動上產生差異。
若此角色得以受到我們認同(由反派印象轉為支援者),乃因為在敘事上,我們曾經跟隨著他踏上馬歇的生活路線,與一眾友好鄰人的陸續會面,而感染、引發了隱藏在他一貫冷酷表情底下的善意:決定護衛男孩順利出海,為故事帶來了童話般的結局。
另一個引發成員們討論的段落,也值得一談。
馬歇化身信差角色,為了舉辦募款音樂會,求助於搖滾樂手小鮑伯和其妻,試圖修復愛情。細看小鮑伯身處的陌生酒吧,前景/背景的構圖較多切割而顯鋒利,而清冷的吧檯景觀僅聚焦於局部,凸顯飲酒者內心的寂寥(只有成排的空酒杯、酒保伸進畫面的手,和小鮑伯黯淡的側臉),再再不同於馬歇社群常去的酒吧。後者是以漸次的分鏡,營造室內的熱絡氣氛,以及主角和熟客的固定位置。
直到,馬歇演出的「愛情天使」和愛人咪咪依序前來,才以劇場式、突兀但未必使人細察的光影轉換,和重複的進/出場方式,標示兩人愛的重逢以及男孩救援的雙重勝利。對於這種乍看不寫實、不自然的處理,有老師表示過程中內心的問號不斷,「導演為什麼要這麼做?」、「怎麼了?」經過一番重讀與解說,若能引發多一些銀幕內外的想像碰撞,對於影視作品中處理現實議題的不同手法,有更多理解與反思。那麼,即使講台上的師者身份不易位移,但無論面對學生或置身校園之外的生活與工作,或許能有更多層次、人文面向的敏銳與耐心。
註一:詳見聞天祥〈來自極地的冷面笑匠〉
註二:關於本片與《波希米亞人》小說和電影的關聯,可見富邦文教基金會翻譯出版的電影單片教材&影評連結:Michael Sicinski, Le Havre: “Always Be a Hu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