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紀錄光影:由外而內的目光
紀錄光影:由外而內的目光
撰文:王志欽(肥內,影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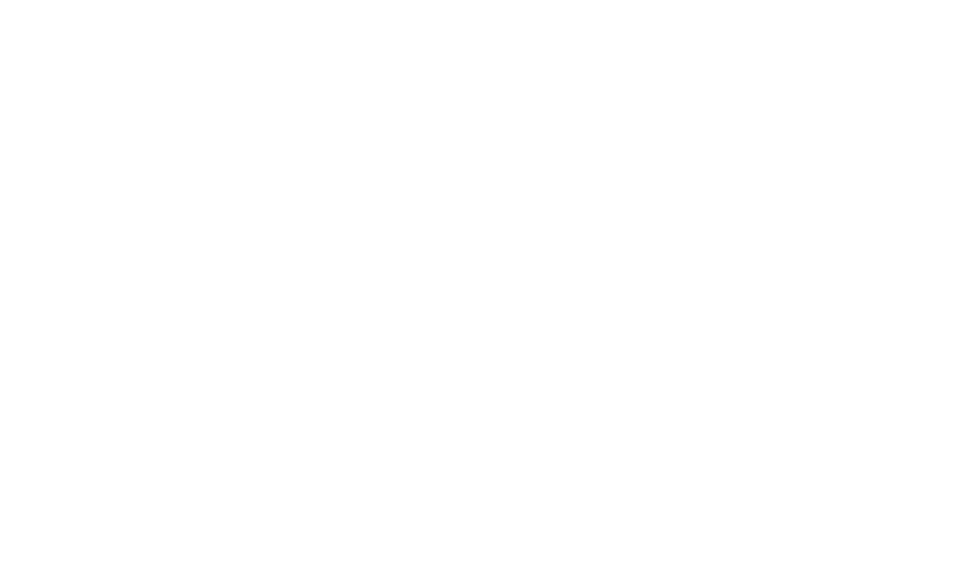
如果有足夠的時間,一同放映《經過中國》(A Trip through China)和鄧南光短片選是合宜的組合。它們的對比性起碼可以在三個面向上產生一些討論:一是製作規模,前者明顯有較多的分工,且可以想像應該製作團隊也較大,後者則像是單人劇組;二是從第一點派生出來的,尤其再加上拍攝目的之後,大概可以對比出拍攝者在後製組織(或不組織)素材時,對於素材的自覺性強度;三則是觀看的目光,亦即拍攝者身分對於被攝素材所起的作用。當然,第三點還能派生出第四個關於拍攝語境的因素,但這兩部片光是語境研究都已經可以寫成論文、出成書了,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要是能對前三點進行適度的討論,足矣。
史料珍貴
以史料保存的角度來看,這兩套作品,或者說,任何影片(尤其是紀錄片)都有它存在的價值,巴贊(André Bazin)也說過,「每部片都是社會寫實片」,所以即使是虛構影片,都還是能看出拍攝當下的語境特點,像是價值觀、審美觀、習慣用語或者思維方式。紀錄片當然更不用說,直接保存了逝去的風光。
像布洛斯基(Benjamin Brodsky)又恰好在民國創立之初身在中國,因此《經過中國》記錄了1912~1915年轉變中的中國樣貌,當然珍貴。而鄧南光這些短片,可以算是在日本政府眼皮下被允許拍攝的民間「寫真家」,在一定範圍內得以自由拍攝當時的景象,多少降低了官方色彩,保留個人的目光,我們如今因而得以一睹1930年代台灣的部分風土民情的寫照,尤其是年輕人的生活狀態。就這一點來説,鄧南光的《有一天》完全可以跟陳耀圻的《上山》合在一起看。
之所以這一段小標說「史料珍貴」而不說「珍貴史料」,當然主要就是著眼於這些畫面對於觀察、研究那個時代的影像,確實是珍貴的,但這個前提是:或許要將影片拆解成「非影片」,亦即,讓這些影像素材還原為「素材」。比如像鄧南光的作品,一般比較看不出創作的自覺,甚至,後製(如果有後製的話)技巧也不算成熟,因此,從影像與影像之間、影片整體結構上,來去推敲這些作品,實際上不太能有所獲。要是對比同時代的外國作品,特別是英國紀錄片學派,鄧南光的作品可以說是相當「原始」的,大概可以類比基頓(Buster Keaton)的喜劇片《攝影師》(The Cameraman,1928)中那位照相師轉攝影師的自學過程。至於《經過中國》則有更強的異國情調想像,且還是以一種帝國姿態的俯視角度來看,被拍攝的中國,僅僅成為某種程度上的怪趣奇觀。
因此故,鄧南光的片尚且還可以原樣播放,但是,《經過中國》的放映,倒是強烈建議可以先挑出幾段(尤其留意不要放到字卡)單獨談一下影像的基本構成,包括構圖、動態、剪接節奏等,然後再交代時空背景,如此看了幾段,大致能感受這些片段的珍貴之後,再重放全片。
詮釋影像
儘管布洛斯基在一定程度上算是逃難(舊金山大地震)來到中國,且還在中國經商致富,但他卻沒有絲毫減弱他的西方優越心態。以這種心境來記錄中國本來也沒有太大問題,然而,透過成片《經過中國》裡頭那些嘲諷式的字卡,很明顯,這部片的預設對象絕不包括中國人——或許,他從來也無法想像中國人懂得看電影。
儘管,在非常少數的情況下,似乎帶有一點人性關懷在裡頭,比如介紹九龍的孤兒院時,不過,這個孤兒院首先是教會孤兒院,多少也是有宣教的意味,但在後來關於上海1914年颱風的段落,又重新使用了孤兒院這裡的部分素材,將之置放在因風災擱淺在港邊的大量船隻以及風災後滿目瘡痍的街景之間,彷彿暗示了颱風帶來的摧殘甚至連人都流離失所,孤兒又得再來這裡收容似的。但姑且不論到底女老師在盲女手上教寫字是九龍的孤兒院,還是上海的收容所,這些影像基本只有一個真相,但透過剪接與素材重複,觀眾已經無法識別究竟這些畫面的真貌。
又或者拿日本工人的工作情況,來對比上海工人的勞動方式,似乎有感中國勞工受到的生理虐待之嚴重;雖說他有意比較日本,大概還是帶著「等級相近的東方國家」有可比性這種心理,於是也讓好意淪為某種餘興。好比,字卡上這麼說「在中國,女性是平權的」然後補充說「在工作這件事上」。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放映時由他自己充當辯士隨片講評時,會是帶著怎麼樣戲謔的口吻來講述,並且引發現場的哄堂大笑!
布洛斯基縱使可能有一個較大的團隊,所以拍出穩定的影像,精緻的畫面看得出對於拍攝主題起碼進行過一些研究與觀察,構圖上大多呈現出相當「正統」的審美情趣。而由於記錄的內容具有普遍性,除了像風災這種偶然情況之外,這意味著他對於拍攝內容還是把握相當的控制力。相形之下,鄧南光的作品,像是名符其實的「持攝影機的人」,單槍匹馬上陣,於是他穿行於祭典、園遊會、博覽會等單一性質的場合,進行既像記錄又像報導的攝錄;或者,像是突來的旅程,比如划船、踏青,或者到(淡水河)河邊踩沙、撿貝殼這類無關緊要的瑣事也會成為被攝對象,因此才說是在一定範圍內的自由。但他作為個人拍攝小組,無疑沒有,可能也沒意識到需要在身為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做區隔,因此,只要不是固定鏡頭,觀眾總有一種拍攝者隨時要衝向前去的印象。拍攝者明顯的在場,也才會拍到像幼稚園兒童在意並凝視鏡頭的這類天真目光。偶爾,比如在《台灣博覽會》中「陸橋」段落,會出現有趣的呈現,因為那一段幾乎都是以俯角方式拍成,攝影機這下倒成為了陸橋。只是,讓人驚訝的是,看到《去看海女》中,海女們大方裸露上身,無疑給人一種強烈的刻板印象落差:原來,當時的人其實是比現代人還開放?(但有趣的是,片中男性反而都穿得比女性保守多了,竟沒看到哪一個是裸露上身的!)
事實上,影像確實不說謊,它忠實地呈現了拍攝者的狀態,乃至於他們透過作品想跟觀眾溝通的東西。紀錄片尤其如此,跟隨著鏡頭的呈現(即拍攝者目光的延伸),它的選擇,已經成為意識形態影像化的第一性,再加上鏡頭與鏡頭、段落與段落的關係,甚至還有文字描述等等,自然是能徹底看穿影像背後那個「大影像師」〔梅茲(Christian Metz)語〕的內心了。紀錄片於是更適合「作者策略」這個批評系統大展身手的領域。
撰文:王志欽
筆名肥內,北京電影學院電影系碩士,臺灣電影學者及著名影評人,曾任職國家電影中心,擔任《Fa電影欣賞》主編,現專職電影文字工作,並於富邦電影學校擔任專業講師,著作有《巴洛克與禪之間尋找電影的空間》。
線上全片觀賞
《經過中國》(Giloo紀實影音)
班傑明.布洛斯基(Benjamin Brodsky)於1912-15年間,自香港一路向北,以電影底片記錄當時中國人民的生活百態、街景與文化習俗,當西方世界開始依賴蒸氣和電氣,中國仍以人力為主要生產力。片中捕捉了不少靠體力掙活的底層勞動者,跟權貴尊榮的富裕有著明顯差異,也與租界及殖民地的繁榮形成強烈對比,為早期中國留下最完整的動態影像。(本片為默片,無對白無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