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薩米的印記》Sami Blood
《薩米的印記》Sami Blood
2016 │ 瑞典SE、丹麥DK、挪威NO │ 彩色Color │ 110 mins │保護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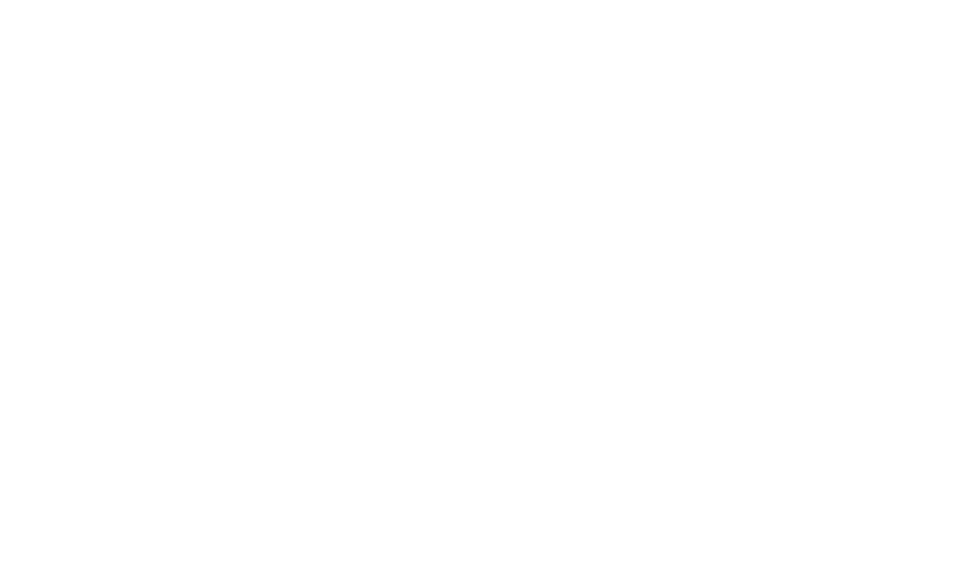
導演:亞曼達柯內爾 Amanda Kernell
《薩米的印記》由薩米族導演Amanda Kernell執導,是她的第一部劇情長片,背景是1930年代的瑞典,講述了北歐半遊牧民族薩米族少女Elle-Marja脫離原生族群、成為瑞典人的故事。
Amanda Kernell的父親是薩米人,母親是瑞典人,父親的原生家庭從事馴鹿放牧,而導演自己的表兄弟姐妹們目前也從事放牧營生。父親相當有意識地向她傳遞關於薩米人的知識,「這部電影是對家族中的老者,以及他們的世代所傳達的愛,其中有些人不希望再與薩米人有任何牽連(中略)。對他們之中許多人而言,薩米語是他們進入學校前的第一個語言,然而進入學校之後,他們僅能說瑞典語。現在他們已經有另外一個名字了,並且說自己是瑞典人,絕口不提自己的過去,與家族失去聯繫。」(可參考導演訪談)
與永遠的局外人站在一起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當社會達爾文主義橫行歐洲之際,瑞典政府深信薩米人是較為低下的人種,「文明化」已無可能,因此針對薩米人的教育政策方針為「教導他們擁有足夠的知識,使其充分受益於自身的境況」,薩米人無法享有與一般瑞典孩童一樣的教育內容、升學管道[1]。雖然強制教育並非為了要使薩米人「融入」主流社會,而是使他們能夠更稱職地進入國家為薩米人所安排的角色,但是學習主流社會語言,仍是現代國家相當有效的控制手段。因此,在片中,我們看到學校裡的薩米族人,被規定無時無刻都必須穿著傳統服飾,卻被要求不得以母語交談。再者,瑞典於1922年於高等教育殿堂的烏普薩拉(Uppsala,也就是Elle-Marja嚮往的有圖書館的城市)設立了瑞典種族生物學學院(Statens institut för rasbiologi),創立者Herman Lundborg將瑞典社會的人口,從至高到最低劃分成許多等級的人種,薩米人毫無意外被放置在最低等的位置,最高等則為科學家;他反對瑞典人與薩米人通婚,並且相信透過研究與測量薩米人的頭骨,可以證明與薩米人通婚生育,將對瑞典種族造成危害[2]。
身為家中長女、學校最優秀的薩米學生,Elle-Marja理所當然成為「典範」,也理所當然成為第一個被推到人類學家的相機鏡頭(如同槍管)的最前線,被「測量」頭骨、被拍攝圖鑑式的照片,在人類學家面前她不過是一頭動物、一團肉。但是在Elle-Marja的主觀感受(此時鏡頭以她的主觀視角拍攝)裡,閃光燈亮得不尋常像砲火,光源處傳出轟天巨響(顯然經過後製),宛如處決人犯;此刻,可以說她身體裡的薩米人被處死了,一位瑞典少女於焉誕生,踏上不可能回頭的、與自身根源徹底決裂之途,成為薩米族群永遠的局外人。
因此,《薩米的印記》不僅僅是少女成長電影,更是一部爬梳了原住民族女性所受到多重噤聲處境的電影;在她的家庭場景裡,父親早逝而缺席,片中的諸多男性角色,看在Elle-Marja的眼裡,就像是環伺的掠食者,無論是等在學校外面的那群少年(少年的結盟總是那麼殘酷),或者是對她舉起鏡頭之槍的人類學家。在這樣的處境裡,Niklas對她而言也許是成為瑞典人的唯一線索,他也努力表現出城市知識份子該有的友善,但是最終與其他主流瑞典人無異,不允許越界,只想要薩米人回到自己的地方與安排好的角色裡。片中大量呈現出Elle-Marja的主觀感受,以臉部特寫,或者是她的主觀鏡頭呈現,更是加深了這份身為「雌性動物」被環伺、被掠食、被剝奪之感,使她必需選擇與主流社會或與原生族群其中一者決裂,這份孤獨也致使她成為敘事的唯一推動者。
片中其他的瑞典女性,在學校受著教育對身體的規訓(整齊劃一的體操),Elle-Marja學習同樣一套體操、換上一樣的衣服、塗上口紅之後,似乎就能真正成為她們之中的一份子,然而事實並非如此,老年的Elle-Marja仍試圖與主流合謀,用跟他們一樣的話語對薩米族群指手劃腳,但是身為局外人的感受依舊強烈:電影開頭那些談論著薩米人的瑞典人,被區隔在畫面以外,Elle-Marja(以及我們這些觀眾)僅是聽到談話聲;開頭的一場葬禮,被她棄絕的同胞向她、向攝影機、向身為觀眾的我們投以敵視不諒解的眼光,她既是主流社會的局外人,也是原生族群的局外人。我們身為觀眾,自始至終被放置在Elle-Marja同樣的位置,我們看見她的觀點、聽見她的聲音,還給她被噤聲數十年以來真正屬於自己的聲音,並且在最後給了她與自身和解的結局。
引導思考問題
- 片中女主角Elle-Marja一共只換了三次衣服(傳統服裝、兩件洋裝、體育服),並燒掉了其中一件。指出並觀察這些場景:這些是發生在什麼情況下?換了衣服之後,Elle-Marja有什麼轉變?這些衣物產生了什麼樣的意義?並且觀察片中其他關於衣著、妝扮的場景。
- 仔細觀察一下片中禁止使用母語的手段:是用什麼說詞禁止學生使用母語薩米語?用什麼方法鼓勵?用什麼方法懲罰?
- 換了衣服、換了語言、換了生活方式,就能成為另外一個人嗎?反過來說,什麼時候人會被規定衣服、被規定語言、被規定生活方式?為什麼權力者要用這樣的手段,而不用其他手段?
- 思考所謂「融入」:什麼是融入?為什麼要融入?誰決定是其中一者融入另一者,而非反過來?
- 到網路瀏覽器上搜尋以下關鍵字:母語、傳統領域,思考《薩米的印記》與台灣當今社會的關連性。
撰文:王詩情
畢業於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紀錄片製作與研究所、巴黎第一大學文化研究所,曾任富邦文教基金會專案企劃、全國巡迴電影學校教材編輯,並曾實際參與發聲電影學校之創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