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山》The Mountain
《上山》The Mountain
1966(2017數位修復)|台灣TW|黑白B&W|19mins|普遍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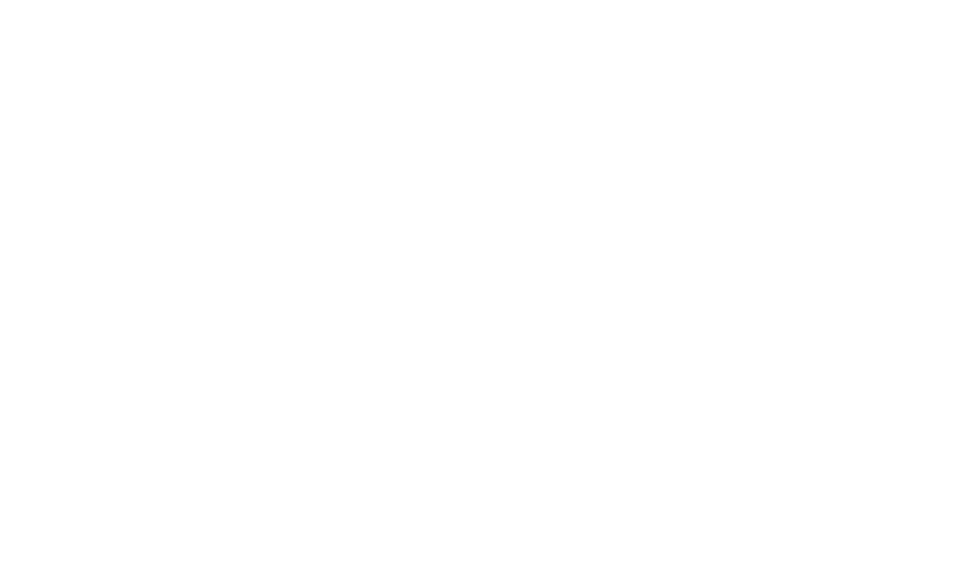
導演:陳耀圻
推薦理由
就讀國立藝專的黃永松、黃貴蓉、牟敦芾三位好友, 熱愛藝術與電影,除此之外的興趣就是爬山。1966年,時年27歲,甫自美國回台導演陳耀圻,於碩士論文作品《劉必稼》拍攝之前,輾轉認識三人。某天,他帶著16mm攝影機,跟著他們造訪新竹五指山,將三人的青春、友誼、路上的風景,收攝至黑白影格之中。一曲〈California Dreamin’〉的配樂使用,不僅烘托了三位青年煥發的活力,與影像之間的對話,更激盪出多重意涵,使得《上山》不只是一次郊遊的紀錄,更是一場精神的漫遊。
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黃永松借宿在觀音禪寺中,準備大學聯考,張照堂隨他登上五指山,消磨炎夏,在一望無垠的山頂上,一時興起,以遼遠的高山景致為背景,拍下黃永松傾斜無頭的裸身背影,苦悶,頹廢的蒼白意象,成為張照堂的攝影經典。加上《上山》,五指山儼然成了60年代兩個重要影像事件的發生場景。
導讀與分析
1967年,陳耀圻的四部作品《后羿》、《年去年來》、《上山》、《劉必稼》,於植物園內的台灣省電影製片廠以及公館的耕莘文教院舉辦放映會。其中以《劉必稼》獲得最多的讚譽,真實電影(cinema vérité)的紀實手法與人物散發出的真摯情感,為瀰漫虛無的藝文界帶來嶄新的氣息。又其獨立製片的姿態,在台灣一片黃梅調、健康寫實、好萊塢的電影之中,顯得秀異難得,亦自此樹立經典地位。然而,早於《劉必稼》製作完成,較少被討論的《上山》,卻在半個世紀後,隨著導演於美國的教授車庫找回膠捲,修復放映之後,影片的價值與其時代意義,逐漸彰顯。
其一,《上山》使台灣電影連接上了世界的電影浪潮。二戰後,不少歐美青年創作者,反感於舊的電影體系以及主流電影的陳腔濫調,對於電影製作、敘事以及電影所描繪的真實有著新的期待與想像。義大利新寫實主義、法國新浪潮、直接電影、真實電影背後的實踐動機可說皆奠基於此。科技的進展(16mm攝影機、收音設備)也間接推動一波波的革新浪潮,這些新型態的影像是個人化、非類型的,直接訴諸現實的,亦致使在這些電影之間有著類似的製作原則與風格:手持攝影機的運用、自由的剪輯風格、低預算、實景拍攝、小人物主角⋯等。而這些特質我們都可在《上山》中發現。
其二,《上山》作為全球青年抗爭場景的反打鏡(contrechamp)。影片折射出台灣弔詭的與世隔絕狀態。在影片的訪談中,陳耀圻問及三人是否得知越南在打仗,有無留意相關新聞。三人表現的毫不關心,暗示出台灣青年對於全球情勢,與此起彼落的青年抗爭風潮疏離。對照當時許多國家青年湧上街頭,大聲呼喊、甚至不惜流血,以暴力手段對抗壓迫體制的場景,《上山》所映照出的青年生活,是如此平靜,甚至有些百無聊賴。如果歷史的全景,是由一片片的碎片拼湊起來,《上山》就彷彿是60年代全球青年圖景的留白影像。
其三,《上山》為幾乎被遺忘的電影夢留下線索。影片裡的三位藝專朋友,在拍攝的當下,都還只是懷著電影夢的文藝青年。我們在影片中感受到牟敦芾不當導演情願死的強大意志。之後,三人好友以當時罕見的獨立製片方式完成《不敢跟你講》,黃貴蓉化名「后方」擔任編劇,黃永松則擔任電影的美術指導,由牟敦芾執導。不久後,牟又完成《跑道終點》。然而,這兩部作品在當年皆因故未能順利正式上映。後來,黃貴蓉婚後不再參與電影創作。黃永松創辦後來家喻戶曉的漢聲雜誌,為保存傳統民俗文化努力不懈。牟敦芾前往香港,拍攝許多邪典電影(cult film),三人淡出台灣電影圈。遲至半個世紀之後,兩部傑出動人的影片終於再度出土面世,使現代的觀眾有機會見證三位好友電影夢想的實踐,也因此三人曾作為電影人的身份才重回歷史的視野。而《上山》不僅留下三位好友的青春軌跡,同時見證了三人電影夢的起點。
訪談:敘事邊界的層層擴延
《上山》的室內訪談容易令人聯想到「真實電影」的代表作《夏日紀事》開場,尚胡許(Jean Rouch)與艾格摩林(Edgar Morin)在室內與瑪索琳娜(Marceline Loridan)談及影片意圖。就在第一段的訪談場景中,陳耀圻也如同尚胡許與艾格摩林,以作者的姿態現身於鏡頭前與三位主角對話,明白的表示其拍片動機來自得知他們放假會去登山,因而有了記錄的想法。
訪談之於影片有著「說明」(exposition)的功能,陳述影片人物身份、情節狀況、場景與發生的時間,共分成九段。一至四段的訪談圍繞在登山的話題,說明了五指山為黃永松自小便經常造訪的地方,特別是山上的觀音禪寺。禪寺的師父為父親朋友,自小跟他多有交流,還提起師父對於信仰的開放心態。五至七段,談話的內容,轉移到三位青年身上,聊起三人的出身背景、結識的過程,以及對未來的想法。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牟敦芾的電影大夢,那由黃貴蓉代為說出的「不當導演,情願死」的強烈意志。八至九段的訪談,有著更大的視野,觸及當年的黨國時代壓抑禁錮的生活,以及三人對於越戰的漠然。從山到人再到世界,敘事的邊界一層一層擴延。
訪談進行的地點是當年黃永松於板橋的宿舍。三人的背後有輛倒放的單車,黏貼著一張張照堂的攝影作品,模糊蒼白的影像,暗示出當年深受西方文化與思潮、存在主義、荒謬劇場、超現實主義影響的現代派美學的文藝氛圍,空間的背景亦是時代的背景。這個封閉空間,連同訪談,鑲嵌在三人上山的影像序列中,仿若在影像的時空中切開通道,如同中繼站般,開啟往昔記憶與未來想像的相遇契機。
透過訪談我們可得知,黃永松曾帶牟敦芾前往,黃貴蓉則尚未到過。因此,片中的旅程是發生於未來。對於過去的描述與回憶,使我們意向著、想像著五指山。因此登山的影像並非「被說明」、「被應證」的記憶影像,而是仍保有空間、未知,可供經驗的相遇(encounter)過程。而導演精準的提問彷彿架起層層歷史場景,凸顯出個人與環境、歷史之間的關係,訪問的段落因而有了景深的作用,映照著三人登山的影像,使得原本單純不過的青年出遊,成了一次來回於城市與自然、世俗與精神、現代與傳統、西方與東方之間的精神壯遊。
而三人中,觀眾焦點所在容易落在黃貴蓉身上。她是唯一的女性,形象上的差異,容易吸引觀眾的目光,另外,在敘事上,她未曾過到五指山的狀態,與大多的觀眾一致,因此在三人中,她的角色較容易取得觀眾認同,透過她投身在故事中,一起上路。這兩男一女的組合也令人聯想到楚浮(François Truffle)1962年的《夏日之戀》(Jules and Jim),在有限的情境裡隱約帶有情感上的張力。
動感的影音調度
如同《劉必稼》,《上山》同樣有著「移動」的母題,在其開場段落已然清楚揭示。第一個鏡頭觀眾即置身於車站,隨後轉移到月台,再到車廂之中。特寫,我們看見一張女性臉龐,她看著窗外,攝影機往左搖攝,窗外景觀入鏡,車站月台與鐵軌,演職員表字卡出現,火車開動使得鏡頭成為推軌鏡頭,街景進入景框又隨即流逝。車站場景、移動中火車、旅人、流逝的風景、攝影機運動為影片建立了移動的基調。
然而相較於《劉必稼》的安靜沈穩,《上山》散發出更強烈的動感氣息。這是有賴於陳耀圻於敘境內外的進行的影音部署所產生的效果。
首先是身體影像的展現。由於未有現場收音,也未有畫外音的敘事牽絆,影片中三位年輕人的身體(臉部表情、身體動作與姿態)儘管有著敘事功能卻無須服膺影像敘事,較語言更具感染力,但擺脫了理性的姿態。例如,黃永松與牟敦芾的腕力遊戲,黃永松拿著木劍指向黃貴蓉,他們在觀音禪寺廂房內的嬉鬧,以及牟敦芾拿著刀大砍野草樹叢,面對野地時身體所暴露出的野性,還有雨中的奔跑,那些特屬於年輕身體過渡時間與佔據空間的各式行動。
另外則是風景的展示。移動的同時,周遭風景同樣地流轉。像是在火車與公車,從城市經過鄉村的田園,最終過渡到山區,步行上山,隨著小徑延伸不斷改變的景致。山上的氣候與天氣變化,也使得三人的登山所歷經的環境時而晴、時而雨、時而霧。而雲、霧、雨也在視覺上形成空氣擴散效果,消彌了事物的形體邊界,表現變動不居的自然面貌。
除了人與風景外,攝影機更是在賦予影像動態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陳耀圻在片中運用手持攝影機,擺脫了腳架的限制,解放了拍攝者與觀眾的身體,更自由地參與人物的行動亦有利於開拓電影空間。譬如,在三人找地方躲雨的片刻,持攝影機的陳耀圻也跟著跑動起來,激烈的影像晃動,給予觀眾如同在場的共感,既感受到三人躲雨的急切心情,亦有著奔跑帶來的解放之感。
也常見導演藉由各種不同視角的拍攝選擇(仰角、俯角、平視),搭配不同的攝影機運動(橫搖、直搖、推軌、變焦)的混合使用,致使景框中的世界產生相對的複合移動。像是三人躺在寺廟房間的一幕,鏡頭在空間中游移,時而特寫、時而近景捕捉三人的影像,持續的來回往返,就在攝影機聚焦在牟敦芾與黃貴蓉的手時,突然高速變焦向前,切接,場景突然轉換到戶外的樹林,黃永松從背景的樹林間衝出,其他兩人在後,三人往小徑的另一端奔跑過去,在這兩個鏡頭之中,攝影機並非被動地捕捉人物運動,反倒像是由自身的運動來誘發人物的行動,最後再透過剪接的空間調度,創造出影像的轉調與變奏。
《上山》也藉由套層的景框遊戲,於觀者心中創造出未盡之感。每一個鏡頭似乎都是未完成,創造出鏡(境)中有鏡(境),有著懸念的無盡狀態。比方,4:35秒左右,鏡頭先是特寫瑞穗橋停車站牌,往右橫搖後,畫面瞬間變成全景,前景為樹林,在背景深處,隱約間看見三人走在山徑上。此外,一方面可能考量取景的限制,一方面為了能讓三人同時入框,影片有著許多的斜角構圖,亦增添影像的動力。
當然,不可不提音樂的使用。1966年的歌曲〈California Dreamin’〉 遍佈在影片中,陳耀圻甚至使用了數個不同版本,這些版本各自有著不同的編曲與樂器配置。這首揉合著藍調與鄉村搖滾的歌曲本身的旋律充滿律動感,加上樂句與影像的對位,輔以音量的調節,與影像之間激盪出強大的動能。歌詞內容描述著離開前往他方的渴望,相應著三位青年遠離城市的上山之旅。歌曲也象徵著西方,尤其是美國為首的文化,包覆著《上山》的影像時空,延伸出美國文化於60年代的主導地位的解讀。而當時美國嬉皮文化回歸自然的傾向,卻在片中意外地與三位青年的旅程有了重合的意義。
除了不斷出現的〈California Dreamin’〉,上山的過程中還有著落雨的水滴聲、傳統戲曲聲、誦經聲、寺廟鐘聲、風聲,除了體現不同的時間感,結構了影片時間外,也呈現了眾聲喧嘩,東西雜揉的文化音景。而這些看不見音源,不同步的音樂與聲響,隱約描繪出60年代的台灣其處於時代錯位與漂浮游離的精神狀態。
委員短評節錄
適合教學環境操作,能夠引領了解紀錄片史的脈絡。——陳俊蓉
數位修復成果驚人,極具時代意義。——王師
訪談議題舉重若輕涉及教育、移民、宗教、性別、政治等討論,能提供不同類型課程開放的討論空間,也能拓展兒少觀眾對60年代紀錄片的全新認識。——Skaya Siku
引導問題思考
- 影片一開始就透露這部片記錄的時間點為1966年的福爾摩沙,也在上山路途強調路標(瑞穗橋、五指山)、你覺得為何要強調時空背景的標記符號?為何導演會使用福爾摩沙?
- 你覺得為何影片選擇在宿舍訪問三人?為何不在上五指山之後再進行訪談?如果也訪問禪寺的師父對於敘事會有何改變與影響?
- 導演的隱身,是否代表沒有作者介入?
- 觀音禪寺的場景中,你覺得為何導演都以剪影呈現誦經的師父?
- 你如何看待音樂在這部片的功能與角色?音樂出現時通常在什麼時刻?搭配的是什麼影像?影片使用諸多非敘境音樂,你覺得會影響紀錄片的真實性嗎?
撰文:蔡世宗
※本影片可於會員專區觀賞全片,需先至會員專區以學校信箱註冊,登入後即可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