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鬪犬》Canine
《鬪犬》Canine
2016|印尼 ID|彩色 Color|65 min|保護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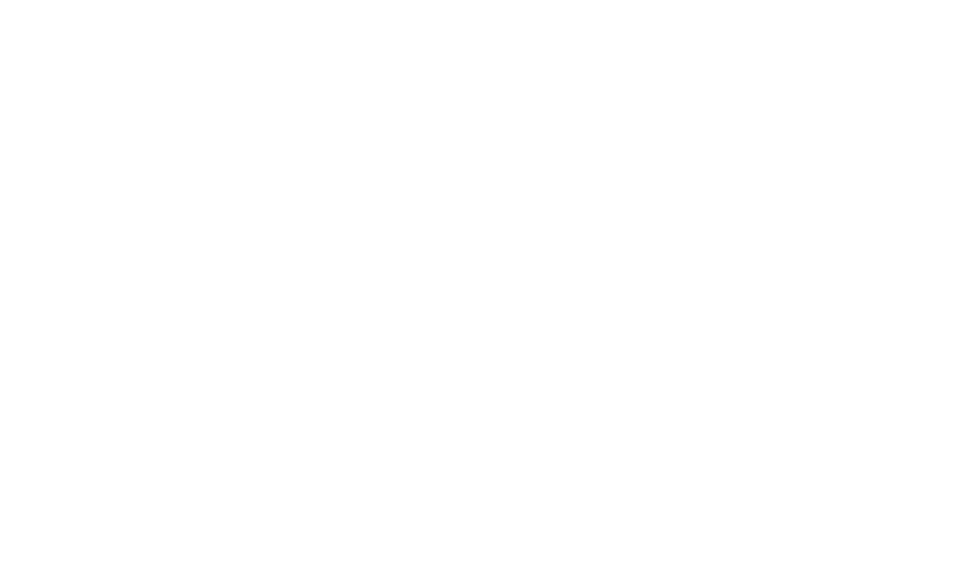
導演:艾沙.哈里.阿克巴 Esa Hari AKBAR
2018年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亞洲視野競賽 評審團特別提及獎
豬狗鬥是印尼西爪哇萬隆地區的一項傳統。然而這項傳統,卻引發傳統文化與動物保育孰輕孰重的辯論。主角小楠上學時,是個戴著頭巾信仰伊斯蘭教的小女生,回到家後她脫掉頭巾,和其他男性一樣對豬狗鬥充滿興趣及熱情。一天,她與父親找到了一隻鬥牛犬後,他們開始對牠展開訓練,並希望在豬狗鬥的比賽中贏得勝利。然而,比賽結束後,卻引發她更多的複雜情緒。透過《鬪犬》這部片,令我們重新思索傳統與現代價值的兩難。
第一部分:導讀與分析
有些紀錄片不採取訪談的形式、不加入旁白或字卡解說、導演並不入鏡而站在旁觀者角度,不介入、不干涉被拍攝對象,在現場等待隨機事件發生。這並不是一種嶄新的紀錄片形式,美國紀錄片導演羅伯特・德魯、梅索兄弟、懷斯曼等人,在五、六零年代創造了以旁觀者角度、不重演、不使用燈光、不介入事件的方式拍攝紀錄片,並認為紀錄片應該純粹的紀錄現實,而這種紀錄片被稱之為「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然而,站在旁觀者角度記錄的「直接電影」,代表著此種紀錄片不存在觀點嗎?
構成電影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是剪接,剪接可以選擇讓故事的真實時間大幅縮短卻又能保留敘事的完整性,也可以選擇以時空交錯的方式鋪展劇情。剪接,也是選擇畫面接續的方式以製造不同情緒及效果;種種選擇的結果,也代表了觀點的形成。
《鬪犬》是一部沒有對白,導演「看似」不介入事件、也不入鏡的紀錄片,影片只在開頭時放了張簡單的字卡,解說印尼西爪哇萬隆地區的「豬狗鬥」傳統。但是《鬪犬》算是「直接電影」嗎?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影像與聲音/音樂的運用,會發現導演事實上以音樂暗示並「介入」觀眾情緒。然而,如果我們提及直接電影,並不是想在這篇文章裡試圖論證《鬪犬》為何是/不是直接電影,而是「直接電影」的形式可以引領我們去觀察在不以作者積極在場表現觀點的紀錄片中,紀錄片的真實與觀點如何呈現?在《鬪犬》這部影片中,即便欠缺訊息式的電影元素(旁白、解說字卡、訪談等),在敘事結構上仍很完整地建構出圍繞在豬狗鬥傳統裡生活的人。影片一開始人們下賭注、觀看比賽、比賽結束;接著,主角小楠跟著爸爸找到一頭鬥牛犬訓練牠比賽。接著我們看到這隻鬥牛犬從一隻不主動攻擊的溫馴動物,漸漸轉變為一頭兇猛的鬪犬;最後牠與山豬爭鬥的過程中受傷。在這個故事的鋪展過程中,導演在鏡頭選擇、敘事建構上,置換許多不同觀點與角度去觸及傳統文化與動物權相牴觸時,所面臨的矛盾及衝突。而這些矛盾與衝突不只來自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也來自於我們對伊斯蘭信仰的某些刻板印象。
在影片第一場豬狗鬥的場景裡,我們除了看到人們如何準備下賭注、比賽,更看到了在二樓圍觀賽事的人們。在這個鏡頭裡,我們會發現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圍著柵欄望著底下互咬的兩隻動物。於是,這個比賽與觀眾裡的年幼孩子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這個傳統對萬隆地區的人們是再日常不過的生活,它是觸及所有性別與年齡的比賽。甚至在影片後面的一場戲裡,我們看到一隻山豬被抓回來和主角小楠的鬥牛犬進行訓練,而小楠的爸爸隨後將鍊住山豬的繩子交給一個大約4、5歲的小男孩。此外,故事以小女孩小楠為核心,於是我們會看到她去上學時戴著頭巾,回到家拿掉頭巾後如同其他男性一樣,對豬狗鬥充滿興趣與熱情。因此,導演在主角性別選擇上,也表達了議題可以拓展的角度。而在鏡頭的選擇上,除了人(包含導演、被攝者、旁觀者等)的角度外,還增加了動物觀點,特別是鬥牛犬的角度。導演將攝影機放在狗身上,在幾個畫面裡我們會從狗的角度看世界,如此,可以跳脫人的視角去接近動物的情緒。從以上這幾個選擇來看,導演透過畫面拓展出議題更多層次的討論,有傳統、性別、動物權;直到影片最後,回到小楠失去鬥牛犬的情緒,也帶出這項傳統在熱情之外的失落,而導演的觀點也在敘事鋪陳的最後悄然確立。
法國人類學者艾德嘉・莫杭曾提到:「有兩種感受電影真實的方式:第一種是試圖去揭露真實;另一種則是提出何謂真實。」《鬪犬》並不意圖揭露豬狗鬥這項傳統面對道德或所謂「文明」上的絕對性,而是透過這項活動,延展出社會中隱而未顯的文化面向。
第二部分:延伸問題
一、當紀錄片中沒有旁白、訪談等形式向觀眾詳細解說某些特定觀點時,你認為影片還可以用什麼方式傳達訊息?以影片中第一場豬狗鬥的場景為例,你看到了什麼?
二、你觀察到《鬪犬》裡有哪些不同觀點的鏡頭?從這幾個鏡頭角度看出去的視角,令你產生什麼樣的情緒?
三、你覺得主角小楠為什麼也想訓練鬪犬?你覺得她在這整個過程中得到了什麼?又或失去了什麼?
四、你覺得傳統文化是什麼?假如傳統文化和現代社會的某些價值觀(比方動物權)相牴觸時該怎麼辦?回到台灣社會,當原住民的狩獵權和野生動物保育法相衝突時,你認為應該怎麼辦?
撰文:史惟筑(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專任助理教授)